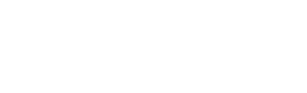奔流不息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突出的统一性,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生成、牢固、凝聚,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这种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不断巩固、中国人民共同生活的疆域和空间不断广大的统一性——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权割据的时代有之,战乱流离的时代有之,但追寻和建设统一稳定的国家始终是历史主流。这种历史主流的形成与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巩固史、共同生活的疆域和空间的拓展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结束了兵祸连连、民受其害的战国时代。这一事件标志着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区域范围的中华核心文明区初步统一。
此后,秦收复河套、南征百越,形成了“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阔疆域。
隋唐时期,“中国一统”重新光大。这一时期,朝廷创设并严密科举制,开凿大运河贯通南北,设置安西四镇和塞外800多个羁縻州府。因各民族交流频繁,造就了渐趋一体的盛唐气象。
到了元朝,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进一步交融汇聚,中华文明区更加扩大。元朝虽然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是它在外交上都自称为“中国”。元朝宗庙祭祀所奏的《威成之曲》中,就明确有“惠孚中国,威靖边庭”等内容。
清朝和元朝相似,虽然前者由满族人建立,但也同样自称“中国”,且其统治者对中国一统的信念更为强烈。在对琉球的国书中,清廷文书写道:“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康熙年间,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清廷明确用“中国”一词与俄国交涉。雍正时期更明确强调,所谓“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正是在这样强大的中国认同与中国一统信念的支撑下,中国的疆域在有清一代最盛时扩展至1300多万平方公里。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上写道:“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中国统一的历史延续性正在于此。
这种统一性,是国家制度建设、国家治理推进的统一性——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创立帝制加强中央集权,以郡县官僚制编户齐民,实现“车共轨,书同文,行同伦”。国家的一统,每一步都紧密结合制度建设与治理推进。
自秦至清,正是因为有这种立足于统一的国家制度建设持续演进、国家治理推进步步完善,所以全国相互依存的政治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网络得到了持续发展。即便在分裂时期,这些网络也得以保留并积蓄力量,等待再一次焕发生机与活力。
这样的“统一基因”,到了清代有了令人瞩目的延伸与发展。清廷因需要统治多民族的广大疆域,专门设立理藩院管理非汉族事务,并对蒙、回、藏等因其风俗而施政。
1636年,漠南蒙古归附,清朝统治者与蒙古族贵族结为政治联盟。对较早归附的蒙古族上层贵族,清廷特别封赐爵位,且允许世袭。对蒙古族各部落的管理则创建盟旗制,旨在防止新部族聚合及旧部族分裂。
同时,满族贵族和蒙古族王公之间长期通婚,总计达500多次。其中,满族公主、格格出嫁者400余名,清廷皇帝宗亲娶蒙古族王公之女150余次。
清廷还允许蒙古族王公赴木兰围场,跟随皇帝狩猎。其用意如乾隆所言:“伊等目睹内地幅员之广阔,人民之富裕,回归上境,自必转相告语,同心向化。”
由此,朝廷得到蒙古族各部强有力的支持,也有力促进与维系了北部边疆的统一和稳定。
在西藏,清廷根据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设置驻藏大臣。噶厦四长官以下的僧俗官员,由驻藏大臣、达赖喇嘛共同拣选。西藏地区的财政事务、对外交涉,也由驻藏大臣负责。达赖、班禅的转世掣签、坐床等,由驻藏大臣主持监督。
在对蒙、藏等族因俗施政的同时,清廷对汉族士大夫推行笼络政策,通过“更名田”“特科”“恩科”、满汉同榜一体科考等进行拉拢。
借由一系列制度、政策的推行,有清一代形成了由皇帝联合满、蒙、汉贵族官僚的统治结构。这从《清实录》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就可见一斑。
以上说的是精英层面,在一般社会层面,各民族的交融同样得到快速提升与发展。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满族与汉族的互动交融,并在文化心理等层面渐渐融为一体。
清廷入主中原,带来不少满族人士的举族内迁。这直接促进了满汉之间自然渐进的交融。康熙中期以后,“旗民地土”相邻,旗人与民人错处,“无界址之分”。
同时,满汉互为婚娶、抱养子嗣,使得混血情况逐渐增多,还有越来越多的满族人使用汉语。到光绪中叶,连黑龙江呼兰旗营一带,语言文字俱从汉俗,“能操清语者则千人中一二人而已”。有人概括:“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
与之相伴,汉族风俗也受到了满族风俗影响,满汉之间经济、语言、文化的一致性愈来愈多,逐渐汇合为“新的文化”。
有清一代,经由国家制度建设、国家治理推进,中国的多民族格局呈现大的更新。各民族的同一部分和共有部分明显增多,可谓“你中有我、水乳交融”。
这种统一性,是中华主体文化长期认同形成和各民族文化在共存之中融汇的统一性——
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其他诸子思想产生于先秦,是百家争鸣的文化结晶,是“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率先突破的典型表现。外来的释家思想,从东汉起传入中国并不断本土化,最终产生了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禅宗。
一方面,我们不断融合在中国产生的多样文化;另一方面,那些外来传入的文化不断本土化、中国化,进而以“家国天下”为基本架构形成与丰富了中华文明。
这样的文化一统之所以能够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影响力,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它在长期的互动中成就了“靖一国之思想,同一国之风气”的氛围与传统。
基于长期、广泛的传播,它还对中国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等地的思想文化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统一的“中国思想文化市场”和较为统一的“东亚思想文化市场”。
进一步来看,中华各民族文化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而具有共存的基础和条件。同时,历代王朝都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作出过努力,推进了融汇的趋势,发展出融汇的结果。
还是以有清一代为例,清前期诸皇帝都重视儒学,希望通过对儒学的扶持强化“满汉一体”。他们还以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自命,以期融入中华主体文化。
比如,康熙就很认同臣下奏疏所言的“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积极推行“经筵日讲”,选取儒学典籍及《通鉴》等有关治乱兴衰之史书而“讲贯䌷绎”。在他主政期间,“经筵日讲”持续15年,共讲授800余次。
康熙还拜谒孔庙,亲书匾额“万世师表”,并恢复孔、颜、曾、子、孟后裔之俊秀者选送国子监读书的制度,即所谓“圣裔监生例”;诏举“博学鸿儒”,各地荐举近200人,中试者50人,俱授为翰林,入史馆修史。
雍正进一步强调儒、释、道“三教之用虽殊,而其体则一”;乾隆则尊崇程朱,屡次下诏褒奖符合儒学意识形态的所谓“忠贞节烈”。
清廷为适应蒙藏地区民众的信仰而尊奉藏传佛教,先后册封五世达赖为“达赖喇嘛”、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敕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等。由此,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变得清晰。
综合史料来看,清前期诸皇帝对儒、释、道等有较深理解,又对满族文化有扶植与坚持,对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从历史到现在,各民族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交融汇聚的灿烂沃土中,深深得益于中华文明在统一发展中所形成的深厚底蕴。
中华民族的伟大来自统一,中华文明的不朽依托于统一。我们要倍加珍惜中华民族共有的统一家园,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不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堡垒构筑得更为坚固、强大。
作者丨于明静瞿骏(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来源丨解放日报
题图丨新华社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