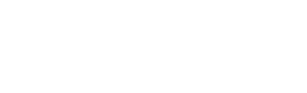杨国荣,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AJournal of ComparativePhilosophy编委,清华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在海内外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其中主要部分收入《杨国荣著作集》(11种,2009年出版)。多种论著被译为英、韩、德等文在国外出版或发表。
学以成人的讨论,既涉及如何理解“学”(何为学)的问题,也关乎如何“成人”(如何成就人自身)问题。以中西哲学的相关看法为背景,可以注意到以上论域中的不同思维趋向。由此作进一步考察,则不仅将深化对“学”与“成人”关系的理解,而且可以在更广意义上推进对如何成就人自身的思考。
为学的广义内涵
“学”在宽泛意义上既涉及外部对象,又与人相关,“成人”则指成就人自身。首先可以关注的是以认知或认识为侧重之点的“学”,其传统可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的德尔菲神庙之上,镌刻着“认识你自己”(Know yourself)。这里的“你”,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人,认识人自身,旨在把握人之为人的特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以上看法一方面意味着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关乎人和神之别:人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在此意义上,认识人自己,意味着恰当地定位人自身。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就是知识”。这里的美德主要是指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正是这种规定,使人区别于其他对象。把美德和知识联系起来,体现的是认识论的视域。作为与知识相关的存在,人主要被理解为认识的对象。以“美德即知识”为视域,与人相关的“学”,也主要展现了狭义的认识论传统和进路。
在近代,对“学”的以上看法,依然得到了某种延续。康德在哲学上曾提出了四个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期望什么?人是什么?”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具有综合性,涉及对人的总体理解和把握。康德对“人”的理解涵盖多重方面,包括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人的规定,以及从价值论的层面把握人的价值内涵。从实质的层面看,何为人这种提问的方式,仍然主要以认识人为指向。就此而言,康德对人的理解基本上承继了古希腊以来“认识你自己”、“美德即知识”的传统。
除以上传统外,对与人相关之“学”的理解,还存在另一进路,后者具体体现于中国的儒学。先秦儒家奠基人孔子的经典《论语》,第一篇是《学而》,其中所讨论的,首先便是“学”。先秦时代儒家最后一位总结性的人物是荀子,《荀子》第一篇即为《劝学》。在儒家论域中,“学”既涉及“知人”,也关乎“成人”,从而表现为知人和成人的统一。这种理解,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关于“学”的主流看法。
理解人的以上视域,在中国哲学中首先与人禽之辨相联系。“人禽之辨”发端于先秦,其内在旨趣在于把握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人禽之辨”同时表现为“人禽之别”。就其以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为关切之点而言,“人禽之辨”所要解决的,也就是“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人的以上把握,在中国哲学中往往更概要地被理解为“知人”。这里的“知人”既涉及人禽之辨,又在引申的意义上关乎人伦关系的把握。
作为人禽之辨引申的“知人”,在中国哲学中常常与“为己之学”联系在一起。此所谓“为己”,并不是在利益关系上追逐私利,而是以人格上的自我完成、自我充实、自我提升为指向。这一意义上的“学”,旨在提升自我、完成自我,可以视为成就人自身之学。与此相对的“为人”,则是为获得他人的赞誉而“学”,其言与行都形之于外,主要做给别人看。在区分“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背后,是对成就人自身的关注。
以“为己”、“成己”为目标的“学”,在中国哲学中同时被赋予过程的性质。在《劝学》中,荀子开宗明义指出:“学不可以已”,这一看法意味着“学”是不断延续、没有止境的过程。作为过程,“学”又展开为不同阶段,与之相应的是人成就自身的不同目标。荀子曾自设问答:“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里,荀子区分了学以成人的两种形态,其一是“士”,其二为“圣人”,学的过程则具体表现为从成就“士”出发,走向成就“圣人”。作为“学”之初始目标的“士”,是具有相当文化修养和知识积累的社会阶层。从人的发展看,具有知识积累、文化修养,意味着已经超越了蒙昧或自然的状态,达到了自觉或文明化的存在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谓“文野之别”。这里的“野”即前文明的状态,“文”则指文明化的形态。荀子所谓“始乎为士”中的“士”,首先便可以理解为由“野”而“文”的存在形态。
与“始乎为士”相联系的是“终乎为圣”,后者构成了学以成人更根本的目标。相对于“士”,“圣”的特点在于不仅仅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知识结构,而且已达到道德上的完美性。正是道德上的完美性,使“圣人”成为“学”最后所指向的目标。
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由“野”而“文”、超越自然状态的成人的过程,离不开“礼”的制约。自殷周开始,中国文化便非常注重礼。“礼”涉及多重维度,从基本的方面看,它主要表现为一套文明的规范系统,其作用体现于实质和形式两个层面。在实质的层面,“礼”的作用体现于对应该做什么与应该如何做的规定。在形式的层面,礼的作用之一在于对行为的文饰,即所谓“为之节文”,这里的“文”便是形式层面的文饰。通过依礼而行,人的言行举止、交往的方式便逐渐地取得文明化的形态。
与礼相联系的“学”,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又与“做”、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礼”的引导之下展开的成人过程,同时按照礼的要求去践行。《论语》开宗明义便指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学”和“习”即联系在一起,“习”的涵义之一是习行,即人的践履。从“习行”的角度看,所谓“学而时习之”,也就是在通过“学”而掌握了一定的道理、知识后,进一步付诸实行,使之在行动中得到确认和深化,由此提升“学”的境界。“学”的以上含义,在中国哲学中一再得到肯定。孔子曾指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这里,“好学”首先体现于日用常行、勤于做事的过程。
荀子对“学”的以上意义作了更简要的概述。在《劝学》中,荀子指出:“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为之”,即实际的践行,“舍之”,则是放弃践行。这里的“为”,也就是以“终乎为圣人”为指向、以礼为引导的践行。在荀子看来,如果依礼而行(“为之”),便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反之,不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舍之”),那就落入禽兽之域、走向人的反面。这里再一次提到了人禽之辨,其涵义则已不仅仅限于从观念的形态去区分人不同于禽兽的特征,而是以是否依礼而行为判断的准则:唯有切实地按照礼的要求去做,才可视为真正的人。实际的践行(“为之”)构成了区分人与禽兽的重要之点。
广而言之,在中国文化中,为学和为人、做人和做事往往难以相分。为学一方面以成人为指向,另一方面又具体地体现于为人过程。前面提到的道德实践、政治实践、社会交往,都同时表现为具体的为人过程,人的文明修养,也总是体现于为人处事的多样活动。同样,做人也非仅仅停留于观念、言说的层面,而是与实际地做事联系在一起。在以上方面,“学”与“做”都无法分离。
“学”既涉及本体,又和工夫相联系
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中,对“学”的理解首先与人禽之辨联系在一起。从狭义上说,“人禽之辨”主要涉及人与动物之别,在引申的意义上,“人禽之辨”同时关乎对人自身的理解,后者区分本然意义上的人和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然意义上的人,也就是人刚刚来到这一世界时的存在形态,他更多地呈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对象,还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里可以看到两重意义的区分:其一,人与动物之别,亦即狭义上的人禽之辨;其二,人自身的分别,即本然形态的人与真正意义上的人之分。
从历史上看,中国哲学上不同的人物、学派不仅关注人禽之别,而且对后一意义的区分也有比较自觉的意识。以先秦而言,孟子提出性善说,后者肯定人一开始即具有善端,这种“善端”为人成就圣人提供了前提或可能。但同时,孟子又提出“扩而充之”之说,认为“善端”作为萌芽,不同于已经完成了的形态,只有经过扩而充之的过程,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他所理解的完美存在。所谓“扩而充之”,也就是扩展、充实,它具体展开为一个人自身努力的过程。从逻辑上看,这里包含对人自身存在形态的区分:扩而充之以前的存在形态与扩而充之以后的存在形态。扩而充之以前的人,还只是本然意义上的人,只有经过扩而充之的过程,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本然意义上的人一方面尚不能归入真正意义上的人,但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可能。儒家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便是指每一个人都具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隐含在人的本然形态中,构成了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内在的根据。后者既区别于现实的形态,也使后天的作用成为必要:唯有通过这种后天作用,本然所蕴含的可能才会向现实转化。
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成人的以上的过程,又与本体与工夫的互动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工夫”和“本体”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本体”的直接涵义即本然之体(original substance),也就是内在于本然之中的最初可能。对中国哲学而言,正是这种可能,为人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内在的根据。以本体为根据,意味着成就人过程既不表现为外在强加,也非依赖于外在灌输,而是基于个体自身可能而展开的过程。
在中国哲学中,“本体”同时被用以指称人的内在的精神结构、观念世界或意识系统。人的知、行活动的展开过程,往往与人的内在精神结构以及意识、观念系统相联系。这种精神结构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价值层面的观念取向及认知意义上的知识系统。成人的过程既关乎“成就什么”,也涉及“如何成就”,前者与发展方向、目标选择相联系,后者则关乎达到目标的方式、目标。精神世界中的价值之维,更多地从发展方向、目标选择(成就什么)等方面制约着成人的过程;精神世界中的认知之维,则主要从方式、目标(如何成就)等方面,为成人过程提供了内在的引导。
以知识、德性等观念系统为具体内容,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地生成、发展和丰富。关于这一点,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黄宗羲曾作了言简意赅地概述:“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精神形态意义上的本体并非人心固有,而是形成于知、行工夫的展开过程。在知行工夫的展开过程中所形成、发展和丰富的本体,反过来又影响、制约着知行活动的进一步展开。在这一意义上,精神本体具有动态的性质。
与本体相联系的是工夫。从学以成人的视域看,工夫展开于人从可能走向现实、化当然(理想)为实然(实际的存在形态)的过程之中。上述视域中的工夫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为观念形态的工夫,即中国哲学所理解的广义之“知”,其二为实践形态的工夫,即中国哲学所理解的“行”,“知”和“行”构成了工夫的两个相关方面。广义之“学”不仅体现于“知”,也包含“行”(“做”),对于后一意义上的工夫(“行”),中国传统哲学同样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在社会领域中,“是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做什么”(从事何种实践活动),往往无法相分。具体而言,人正是在参与政治实践的具体过程中,逐渐地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的动物”(政治领域中的主体);在从事法律的实践活动中,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包括成为守法的公民);在伦理、道德的实践(包括儒学所说的“事亲”、“敬长”等等)过程中,成为伦理领域中的道德主体。广而言之,正是在社会领域展开的多样践行工夫中,人逐渐成为多样化的社会存在。
“学”既涉及本体,又和工夫相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学”应有所“本”,这里的“本”既指本然存在中所蕴含的成人可能,也指内在的精神世界、观念系统。“学”有所“本”则相应地既意味着以人具有的内在可能为学以成人根据,也指“本于”内在的精神世界展开“为学”过程。在学以成人的过程中,一方面,“学”有所“本”,人的自我成就离不开内在的根据和背景,另一方面,“本”又不断在工夫展开过程中,得到丰富,并且以新的形态进一步引导工夫的展开。
德行和能力制约着人的自我成就
作为本体和工夫的统一,“学”所要成就的,是什么样的人?从现实的方面看,人当然具有多样的形态、不同的个性。然而,在多样的存在形态中,又有人之为人的共通方面,其一是德性,其二为能力。中国古代哲学曾一再提到贤能,所谓“选贤与能”,便将贤和能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的“贤”主要与德性相联系,“能”则和能力相关。从学以成人的角度看,德性和能力更多地从目标上,制约着人的自我成就。
上述意义上的德性,首先表现为人在价值取向层面上所具有的内在品格,它关乎成人过程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标,并从总的价值方向上,展现了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与德性相关的能力,则主要是表现为人在价值创造意义上的内在的力量。人不同于动物的重要之点,在于能够改变世界、改变人自身,后者同时表现为价值创造的过程,作为人的内在规定之能力,也就是人在价值创造层面所具有的现实力量。
德性与能力的相互关联所指向的,是健全的人格。人的能力如果离开了内在的德性,便往往缺乏价值层面的引导,从而容易趋向于工具化与手段化,与之相关的人格,则将由此失去价值方向。另一方面,人的德性一旦离开了人的能力及其实际的作用过程,则导向抽象化与玄虚化,由此形成的人格,也将缺乏现实的创造力量。唯有达到德性与能力的统一,“学”所成之人,才能避免片面化。
从学以成人的角度看,这里同时涉及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已经开始自觉地关注并讨论这一问题。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和《美诺》篇中,德性是否可教便已成为一个论题。在这方面,柏拉图的观点似乎存在某种不一致。一方面,他不赞同当时智者的看法(认为德性是可教的),并借苏格拉底之口对此提出质疑:“我不相信美德可以教。”另一方面,按照“美德即知识”这一观点,则美德又是可教的,柏拉图也认为“如果美德不可教,那就太奇怪了”。从总的趋向看,柏拉图主要试图由此引出德性的神授说:美德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教育获得,只能通过神的恩赐而来。
较之柏拉图,中国哲学对上述问题具有不同看法。按中国哲学的理解,不管德性,抑或能力,都既存在不可教或不可学的一面,也具有可教、可学性。中国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以“性”和“习”之说为其前提。从孔子开始,中国哲学便开始讨论“性”和“习”的关系,孔子对此的基本看法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里所说的“性”,主要是指人的本性以及这种本性所隐含的各种可能。所谓“性相近”,也就是肯定凡人都具有相近的普遍本性,这种本性同时包含着人成为人的可能性。作为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形态,“性”是不可教的:它非形成于“教”或“学”的过程,而是表现为人这种存在所具有的内在规定;人来到这一世界,就已有这种存在规定。所谓人禽之辨,从最初的形态看,就在于二者具有相异的存在规定(本然之性)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同发展可能和根据。与“性”相对的是“习”,从个体的层面看,“习”的具体内涵在广义上包括知和行,这一意义上的“习”与前面提到的工夫相联系,既可“教”,也可“学”:无论是“知”,抑或“行”,都具有可以教、可以学的一面。
与德性一样,人的能力既有其形成的内在根据,又离不开后天的工夫过程。王夫之曾以感知和思维能力的形成为例,对此作了简要的阐述。在他看来,“目力”(目可视)、“耳力”(耳可听),“心思”(心能思)这一类机能属“天与之”的“性”,它们构成了感知、思维能力形成的根据,作为存在的规定,这种根据不可教、不可学。“明”(目明)、“聪”(耳聪)、“睿”(智慧)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感知和思维能力,这种能力唯有通过“竭”的努力过程才能形成。中国哲学对能力形成过程以上理解,同样注意到了内在根据与后天工夫的统一。
以德性和能力的形成为视域,学以成人具体便表现为“性”和“习”的互动,这种互动过程,与前面提到的本体和工夫的互动,具有一致性,二者从不同方面构成了学以成人的相关内容。当然,如前所述,人的现实形态具有多样性。然而,从核心的层面看,真实的人格总是包含德性和能力的统一,后者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自由人格的表现形式。要而言之,一方面,学以成人以德性和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为指向,另一方面,作为德性与能力统一的真实人格又体现于人的多样存在形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