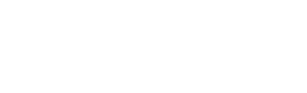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都市城郊农民市民化及耕地闲置的情况越发普遍。近一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土离乡到城郊务农,与“农民工”相类似,该群体可被称为“农民农”。他们蜗居在城郊一隅,却承担了城市农业生产与农产品供应的重要功能。而与农民工、农民等所受到的社会关照不同,“农民农”得到的关注却显得非常之少。来自华师大的一群学子,历时3年对此予以了深入调研,相关课题成果日前斩获了“上海挑战杯特等奖”。
青年报记者刘昕璐实习生曹稔苹
一次家教后“老师”大哭一场
调查的缘起还要追溯到2009年的那个寒假。当时还在读大一的李露萍前往闵行区塘湾村陈刚小朋友家做义务家教,在那里,她目睹了这家人的艰难生活,临走时,所有情绪刹那间迸发,大哭一场,经多次思索后,她决定为他们做些事情。
“从一条车水马龙的道路走进一条泥泞的小路,路两边白茫茫的一片大棚,沿着田埂上错落地搭建着简易的窝棚,一切的一切,都与马路对面的繁华都市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露萍这样描述塘湾村的环境。陈刚的屋子,那是用塑料膜搭建、不蔽风雨的小屋。陈刚的妈妈开始跟李露萍讲述着一家人来沪务农、为孩子治病、晚上12点就去菜场占位等等故事,李露萍听着,觉得心里很压抑、难受。“简直不能想象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十多年。”她说。
李露萍的田野访谈使她在此期间完成了《塘湾菜农生活调查笔记》等一些课堂作业,但是,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却并没有就此罢手。由于觉得自己理论修养不足,同时为了更深一步的调研,2011年起,李露萍陆续邀请到方筱等其他6名优秀学子的加入,力图从学界的相关研究着手,进而更深入地了解“农民农”的相关情况。
2012年5月,7人团队正式成立,12月份团队开始主体调研,全校共有近百名志愿者加入,足迹遍布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闵行、奉贤、浦东7个区21个村,团员们在此基础上从地域空间、经济地位、职业身份、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心理五个层面描述该群体的生存现状,全景式地展现了他们边际生活的困厄。
“农民农”收入几乎是全市最低层
调研团队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民农”都是蜷缩在不蔽风雨的屋子里,这些屋子的屋顶由废旧的大棚塑料和化肥袋子铺成,窗户几乎没有,家具、自来水都没有,二三十户人家公用着几个水龙头,街道上污水横流。
有些“农民农”直接在暖棚中生活,由于作物需要高温,棚内没有任何降温设备。4月份的时候棚内温度已经达到30摄氏度以上,走进一大棚中访谈,出来时已经满头大汗,而“农民农”要在里面生活,忍受一整个夏天。”方筱心疼地说。不过,那些“农民农”却总说习惯就好之类的话。他们认为自己这把年纪能够有份工作就已经很幸运了。
据了解,从全国来看,“农民农”群体的规模达到300万,上海外来务农人员在12万人以上,约占全市农业人口的三分之二。
调查显示,就经济收入的总体状况而言,“农民农”全年人均收入不足15000元的占到43.5%,同期,上海收入最低保障线人均年收入为16800元。近半数“农民农”并未达到上海最低收入的标准,而同期上海农民工的人均年收入为27624元,远高于“农民农”群体。可以说,就收入水平而言,“农民农”群体几乎就是城市的最底层。
建议建立机制使该群体融入社会
事实上,对生活的低满意度,使得他们在强烈的离沪愿望与留在此地间徘徊。“想走啊,经常想。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看看小孩还要读书花钱,也就忍下来了。”在浦东新区务农的黄先生来自安徽,16岁开始种田,来上海已有20多年。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农”特殊的身份和边际社会地位,也使其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没有医疗保险,多数农民农选择“扛病”或“忍病”。上海“农民农”群体未被纳入上海医疗保险体系,仅有27.46%在上海获得了农业补贴。“补贴不到,我们老板(承包商)都拿走了。”徐女士说。
此外,个人能力匮乏与素养缺失,让他们更加边缘。“种菜肯定是苦的,但是没有办法,文化水平就这样,也没有多少环境卫生知识。”这是当地一位农民对“农民农”的描述。
经过3年的调研和时间,《都市庄客:城郊“农民农”群体的编辑生存与发展对策研究》课题,近日斩获“2013年上海第十三届挑战杯特等奖”,这是对他们调研的鼓励。
据了解,团队还就如何改善“农民农”群体生存状况尝试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除了提升社会各界对“农民农”的主观认知,变革现代都市农业产业模式要加快都市农业改革力度外,在团队看来,完善“农民农”各类民生保障势在必行。
另外,政府和社会应当以各种机制促进“农民农”群体融入城市社会,而当地居民与“农民农”群体自身要打开心灵,接纳彼此,不断提升相互走近的动力,而“农民农”群体自身也要充分意识到提升个体人力资本(个人素养)的迫切性。
《青年报》日期:2013年10月9日版次:A09 作者:刘昕璐 实习生 曹稔苹
链接:http://app.why.com.cn/epaper/qnb/html/2013-10/09/content_171076.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