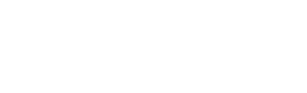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成
冷战后,两极体系终结和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仍在持续,进一步彰显各地区对于全球治理的独立价值。地区问题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议程中的优先方向。中亚地区因其枢纽地位、丰沛资源等因素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基于全新权力配置和国家关系组合的新地区秩序轮廓初显。
现实状态——中亚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
当前,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从内部看,一方面,中亚国家一体化进程渐趋缓慢甚至停滞,而去一体化的症状愈发明显,且有不断加速之势。作为苏联解体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中亚国家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地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不时发生边境纠纷与冲突,民族问题、水资源分配、天然气进出口等问题多次干扰区内国家关系。中亚国家当前彼此间贸易额在各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不足5%;相反,囿于同为资源类产品的出口国,它们在争夺出口市场方面反而多有竞争。种种迹象显示,中亚一体化进程迄今为止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远景目标。
另一方面,西亚北非国家的政权更迭成为影响中亚国家当前政治与安全事务议程设置的关键要素,维持现政权的“体制安全”成为它们2011年以来治国理政的首要目标。虽然中亚各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独立以来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等层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其内部仍然存在各种不稳定因素。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人口结构等各方面来看,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亚成员国都和那些发生政治动荡的西亚北非国家较为相似。它们的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执政当局的制度设计能力和国家治理效率。
哈萨克斯坦石油小城扎瑙津2011年底发生的暴力冲突以及近两年来本为中亚安全港湾的哈萨克斯坦成为恐怖主义活动重要目标这一事实都表明,中亚各国当局的风险管理压力近期在不断增加。一个风险较高、突发事件增多的发展周期可能正在到来,尽管现政权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有望保持总体稳定。
从外部看,一方面,始于2010年7月的“喀布尔进程”实施前景的不确定性已日益凸显。随着2014年美国从阿富汗逐步撤军,阿富汗形势将重新成为牵动中亚地区格局嬗变的重要外部因素。不排除塔利班卷土重来的可能。一旦阿富汗安全情势再度恶化,作为阿富汗邻国的中亚国家势将直面新一轮外溢冲击。
另一方面,俄罗斯、美国、中国等外部大国介入中亚事务的力度较前更大,且彼此之间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俄总统普京今年内已经两访哈萨克斯坦,并依次到访其他中亚诸国。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关系也取得新进展。乌兹别克斯坦决定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新动向都表明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
国际环境——小国外交重要程度不断上升
此外,小国在地区秩序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地位正在不断提升。与历史上多数时期小国往往沦为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不同,冷战结束以来,小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较前有了更大的空间,使其有可能发挥超出其实力与地位的国际或地区影响力。导致小国外交的重要程度不断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增加使得小国发言权加大。国际机制和规范中“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原则在后冷战时期得到了越多越多的体现与贯彻。
而上合组织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以协商一致的原则来推动彼此间的合作,从而在事实上践行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中亚国家与中俄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附庸国与主导国、仆从国与宗主国的等级关系。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并未被动地受制于中俄,不仅在构建对外关系方面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而且在本组织内部议程设置上具有平等的权利。
第二,大国间依然存在的竞争因素逆转了小国的“脆弱性”,使其相对影响力更为“强大”的机会增大。虽然小国经济相对落后,军事力量弱小,且多为国内形势不稳定的国家,但小国所处地理位置,往往在大国抗争中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大国出现持久争夺的情况越来越多,因而它们对于小国的要求和立场不得不变弱。最为关键的是,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受两极对抗格局支配,两大集团内部相对容易形成共识,迫使加入其中的成员国不得不接受。而在后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利益多元化和彼此关系的多样化都使得小国有了更多的外交活动空间。
第三,非传统安全议题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决定了在这些安全问题上大国和小国的相互“嵌入”。安全议题的全球化,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迫切和突出,要求国家不分大小,密切合作。而无论是高科技领域,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领域,甚至是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的蔓延等,非对称性回应能力的拥有都让小国不再处处受制于人。这也意味着,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随着安全问题重点地区转移,小国的作用和地位也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对小国较为有利的变化。
中亚国家可以说是“小而巧”的典型。自各国独立后,尤其是“9·11”以来,中亚国家对外行动的逻辑开始深深影响着本地区其他大国的行为选择,从而对地区格局的形塑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外部大国和国际组织在中亚国家多元平衡外交战略的环境中好似巨人身着重重铁锁,失去了任意行动的自由,而相对于它们作为“小人国”的中亚国家却在某些时候、某些地点拥有更加有力的特征。
基本情境——大国小国构建复合权力架构
复合的权力结构模式对当下的中亚地区格局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即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强大的美国、作为规制性强权的欧盟以及区内强权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起构建了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明网络。在这种大国与地区小国相互构建的复合的权力结构体系框架内,各个参与方并不能在相互关系的所有领域获取绝对的优势地位,从而与其他方形成复杂的权力互动。其中,中亚由于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得到了主要大国的关注,引起它们的竞争乃至对抗,同时也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要求大国之间在事关整个地区利益的问题上抛弃陈见,进行一定限度的合作。这就增加了外部大国对中亚小国的利益需求。
整体看,苏联解体后,伴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结构变得非常复杂。大国关系在该地区的实力分配逐渐演变为类似于一个复合的多维棋盘格局,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是相互关联的不同层级并且呈现出从单极到两极到多极的不同特征。
政治上,“制度安全”的优先考虑使得中俄两国,尤其是俄罗斯,拥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暂时难以比拟的认可度和亲近度。“友善-敌意”的二元模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俄两国与中亚国家的地区认同是相当初步的,目前仍主要是基于历史发展经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其自身的利益考虑,实质上是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一种积极的政治回应,尚不具备可持续性,但相较于美国和西方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经济上,中亚地区的权力结构是更为复杂的多极地区体系:贸易合作中,中俄的影响力逐渐靠近,并且中国已超过俄,可以说是一种两极格局;投资方面,美国先声夺人,中国迎头赶上,俄罗斯正在回归,三方各有所长;在对外援助方面则是美国一家独大,欧盟稳步增加,中国近年来的援助规模也在扩大。在贸易、投资和援助的三角中,总体而言,俄的昔日优势日益受到中美欧等其他外部力量的挑战。
军事方面,俄美形成了两极格局,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俄形成了统一阵线,但三国以及中亚国家都希望本地区能保持和平安宁,解决阿富汗问题以及打击三股势力成为各方的共同利益。
人文方面,苏联遗产确保了俄能够拥有中、美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中、美以及其他外部大国和国际组织暂时都难以与俄的影响力分庭抗礼,形成了残存的单极格局。
长远看,今后在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中亚地区格局不仅取决于大国博弈的阶段性结果,也取决于中亚国家的政策变化并可能出现各种复杂动向以及不断变幻的合纵连横局面。各方同时并存、相互对冲、得失交替会是一个基本特征。
《文汇报》 日期:2012年10月16日 版次:07 作者:杨成
链接:http://wenhui.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2-10/16/content_6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