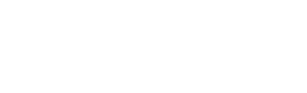梁漱溟说他毕生思考的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而对这两大问题的思考,都把他引向他毕生诠释和捍卫的中国文化。冯契除了在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之间寻找结合点之外,还下更大力气把这两个问题与中西哲学史上的学术问题结合起来,而他在这三者交叉的问题域中的不懈探索,都把他引向他终生构筑的“智慧说”或“广义认识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冯契文集》修订版,不仅对上世纪末出版的该文集初版进行了全面修订,而且在原来十卷之外又增加一卷,其中收入的冯契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期的通俗读物和晚期的讲课记录,可以让读者们对这位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广义认识论”是如何“广义”的,他的“智慧说”是如何“智慧”的,有一个更加具体生动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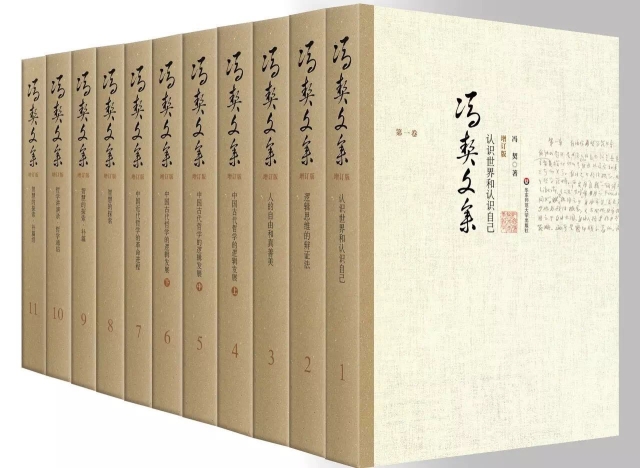
《冯契文集》(修订版),冯契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778.00元
冯契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冯友兰和汤用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幸接受过这样纯粹而全面的学术训练的哲学家,不算太多。但冯契又去过延安,听过毛泽东讲课,并且一再强调他初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时所受到的思想震撼。对于冯契来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篇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阅读《文集》,冯契对这个政治命题的哲学解读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问“中国向何处去”,不仅是问“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向何处去”,而且是问“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个体成员向何处去”,是问中国人如何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站立起来”,而且在人格上、在文化上、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在我看来,这样的追问,恰好汇聚了冯契作为一个个人对自己人生问题的思考、他作为一个国民对社会时代问题的思考、他作为一个哲人对哲学学术问题的思考。

左起:冯契、吕笃周、邓艾民,1943年摄于西南联大
在冯契那里,中国人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意味着找到一个王国维所说的既“可信”又“可爱”的价值王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冯契强调这样的价值王国一方面是从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中提炼出来的,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创造性实践逐步变成接近真善美理想的美好社会和自由人格。如果说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收入《文集》第十一卷),是通过刻画那些受压迫遭侮辱的小人物来表达对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向往的话,他晚年完成的哲学史著述和哲学理论著述,则是通过对中西哲学成果的提炼、综合和发展,来表达对这种社会和人格的深层理解和深刻论证。
就哲学史的研究而论,冯契曾被称作是“以一人之力”完成从先秦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哲学史著述的第一人。中国古代的哲学发展漫长而独立,所以冯契写了三卷《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文集》第四至六卷);中国近代的哲学演变曲折而多因,所以冯契写了一卷《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第七卷)。冯契对中国哲学的回顾总结,同时也是他对中西哲学传统的比较和对话;他一方面用西方哲学成果研究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传统,另一方面用中国哲学的智慧来超越西方哲学对认识论的狭义理解。
就哲学理论的研究而论,冯契把自己超越西方“狭义”认识论的理论体系称作“广义认识论”或“智慧说”(《文集》第一至三卷),这既是冯契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来批判评价西方哲学的结果,也是他反过来用西方哲学成果来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及其论证的成就。冯契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他更重视作为两者之结合的“实践唯物主义”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冯契虽然也重视毛泽东的《矛盾论》,但他更推崇的是系统运用辩证思维的《论持久战》;他虽然也重视毛泽东的《实践论》,但他更推崇的是明确提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冯契那里,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革命家传统”与“学问家传统”汇聚起来了:经过对毛泽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与金岳霖“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命题之间的相互诠释和相互融合,冯契提出了他自己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著名观点。冯契不仅在金岳霖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理论”如何“得自现实”并“还治现实”,而且把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的“还治现实”,分析成两个方向:方法和德性。在“理论”向“方法”和“德性”的转化中,理论不仅得到了运用,而且得到了完成:抽象理念在这里获得了具体生命。
这种意义上的作为方法和德性之基础的理论,可以说就是把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把理性与情感统一起来、把真善美统一起来的“智慧”;冯契晚年完成的“智慧说”,因此既可如他自己所做的称为“广义认识论”,也可以根据其内容而称其为“广义价值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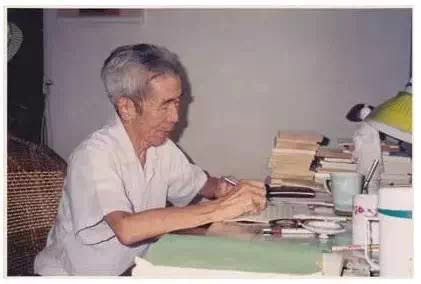
写作时的冯契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冯契强调真正自由的行动是理性的“自觉原则”与意志的“自愿原则”的统一。冯契高度肯定西方哲学对自愿原则的重视,但他不仅强调自愿的意志选择要获得自觉的理性指导,而且强调意志的可贵品格除了意志的自愿性之外还有意志的坚定性。在冯契看来,如果说重自觉原则而轻自愿原则容易导致听天由命的宿命主义,那么,重自愿原则而轻自觉原则,则容易导致随心所欲的意志主义。冯契高度肯定中国哲学对自觉原则的重视,但他认为,中国人所尤其擅长的“辩证理性”精神,只有与西方尤其发达的实证科学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现代科学方法,并且避免蜕变为诡辩论;中国文化足以自豪的理性传统,必须与“以理杀人”的独断主义划清界限,才能避免导致宿命论及其另一个极端即虚无主义。在冯契看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危险,是独断主义的唯我独尊与虚无主义的没有操守的轮流登场,是资本主义的金钱崇拜与封建主义的权力崇拜的同流合污,或者是铁板一块的集体主义与散沙一盘的个人主义之间的非此即彼。
《冯契文集》共11卷,基本上收全了目前能找到的冯契著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冯契长达六十多年的著述生涯中,有一个时期是空缺的,那就是那个通常被称为“十年内乱”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刚开始,冯契的所有手稿、笔记,连同书信和日记,就都被“小将们”抄家没收,至今下落不明。冯契很少谈论他的文革遭遇,尽管他有那么多理由去控诉和抱怨;他也很少谈论自己的不凡经历,包括在1956年10月发表题为“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著名文章,以及在1957年出版《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以后,毛泽东不仅自己认真研读,还向他身边工作人员郑重推荐。但是,我作为学生倒不止一次听到他说,他自己的思想显然也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也曾受到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
冯契对自己的“智慧说”或“广义认识论”的身体力行和“德性自证”,不仅表现为他不断反省而又宠辱不惊,而且体现为他不断探索而又一丝不苟。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冯契与他的金冯两位老师作一个比较。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手稿在躲避日寇空袭中丢失了,他只好在抗战后期直到建国前夕,把这部出版后有千页之多的大书,一字一句全部重写;冯友兰先生在晚年觉得有必要对其早先做了几轮的中国哲学通史著述进行彻底反省,于是,从1980年到1990年,在84岁到95岁的高龄,一字一句书写和口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总共七卷。同样,从1978年开始,年过花甲的冯契在他校园寓所的简朴书房里,在几十年积累的笔记和手稿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在参与、主持和指导各层次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一字一句地写出了《冯契文集》中收入的大部分文字。可以这么说:在人生、社会和学术交叉的问题域中不懈探索的这位当代中国大哲,不仅通过“写什么”,而且通过“怎么写”,为世人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