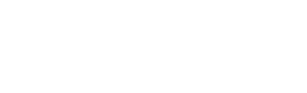我们现在既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讲中国的崛起或中国和平崛起。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选择前一种表述。因为崛起的主体是从无到有,是陌生的,是需要审察认识的;而复兴的主体则是重新归来者,从而是可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供人温故知新者。因此近日施密特与基辛格对话共论中国之际,曾非常明白地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从未有抢夺别国领土的传统。至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大国,我并不认为中国会背弃这一伟大传统。”他信任中国,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历史传统,并因之而有一个可以认识的本来面目。
19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以朝贡体系为主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曾在东亚建立起一种局部的世界秩序,一种大体上可以和平相处的世界秩序。自从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达到东方之后,朝贡制度便常被拿来与之相比附,并在各种解说中往往走样。其实就其本来面目而言,朝贡与被朝贡既不是用武力的强势逼出来的,也不是由经济的强势逼出来的。在近代之前的两千年漫长岁月里,中国能够影响周边并在实际上深度影响了周边的,主要靠的是文化。
惟其如此,辛亥革命后十年,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犹直言“有人认为自从有了日本这个国家就有了日本文化,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用现代的话来说,所谓日本文化,其是东亚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又说“日本依赖中国文化形成自己文化的时期相当漫长,其政治、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点逐步完成的”。他叙述了一种历史事实,也表达了一个历史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敬意。而同日本相比,朝鲜与越南在地域上更切近中国,在文化上也更切近中国,其间先后在他们的国家里建立的科举制度尤其典型地表现了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仰慕,以及自进于中国文化范围之内的愿想。因此,作为一段具体的历史,以朝贡维系的宗藩关系,是实现于中国文化向周边传播和周边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之中的。就其历史内涵而言,周边对中国的朝贡,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朝贡。与之相表里的另一面是,宗藩关系以“事大字小”为应有的伦理。这种伦理决定了中国对藩属是权利小而责任大。藩属以朝贡为礼仪,而中国则在藩属有难之日不能不出力扶持。近代中国的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自身正在困境之中的中国人正是被这种宗藩责任拖着进入历史漩涡的。而究其底里,这也是中国文化能够感召远人的地方。
与这种以文化影响周边的历史相比,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化历史过程重重震荡,并在震荡中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在剧烈变迁中的步步破裂。中国的近代化起源于向西方借法,之后,由19世纪而20世纪,中国人先后以日本为师、以美国为师、以俄国为师,与此相对应,是中国先后出现过日本化的时代(清末新政)、美国化的时代(国民政府)和俄国化的时代(共和国前期)。
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则是外力逼迫下的中国人越来越急迫地向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追究积贫积弱的责任,并以其口诛笔伐的言之滔滔,直接促成了时起时伏,而又四面弥漫于社会思潮之中的激烈反传统和全盘反传统。由此形成的推论以能够接受现代化的中国只能是一个没有历史文化的中国为理路,而表达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和屡起屡挫之后的愤怒和意气。随之而来,是中国的自我形象在人心中的节节破碎。
比之日本的明治维新一面接入“文明开化”,一面又自觉地守定形成于自身历史和文化之中的“和魂”,中国人所经历的这种引西潮、反传统是一个深度搅动和大幅度搅动的过程。其直接的结果是现代化还没有实现,中国在文化上已丧失了自我。而后,是曾经在两千多年岁月里以文化影响了东亚的中国人不得不转过身来,变为文化上的被影响者和被支配者。而本应承担文化自觉的知识人,则身在风会所煽和相互影响之中,成了最难自立骨架的群体。这种由历史留下的惯性至今还没有消失。
三十年来,我以读史为业。而多见的是西人说冲击反应,我们也说冲击反应;西人说在中国发现历史,我们也说在中国发现历史;西人倡社会史,我们也倡社会史;西人倡区域史,我们也倡区域史;西人倡后现代主义,我们也倡后现代主义;西人倡新文化史,我们也倡新文化史;西人倡城市史,我们也倡城市史;西人倡生活史,我们也倡生活史,等等。产出于西方世界的这些史学流派和史学理论不是没有道理,但它们的因果、问题和理路都来自它们的那个世界,从而它们的因果、问题和理路未必都是中国人的因果、问题和理路。我们指望用这种办法与西方人对话和接轨,但没有自己的因果、问题和理路,则对话和接轨无异于应和而我们仍然是受众。
三十年来,出自西方的各色史学流派和理论潮来潮去,灌入了种种新的名词和新的表述。而来去之间所留下的稳定的东西、固化的东西和可传承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其原因所在,一方面,是彼邦的史学流派和理论自成一种尺寸而没有办法罩得住中国历史的事实,以及中国人对这些事实的深度思考。另一方面,是引来这些东西和景从这些东西的中国人太过全神贯注地跟着走和照着做,遂使其中本有的合理性始终成为一种不能内在化而进入中国历史中大问题和核心问题的夹生东西。而跟着走和照着做,显然都是缺乏文化上的自我意识。
现在都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入。这里的中国人当然是指知识人,由此常常会形成自负。但很少有人注意的是,在知识人,尤其是年轻知识人中也常见对美国的了解比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入者。而这一面显然是不值得自负的。19世纪以来的近代化变迁,造成了中国社会里知识人和大众脱节,沿海和内地脱节,城市和农村脱节,制度、思想的变迁和社会的基层结构脱节。身在这种历史造成的脱节之中,而取法的榜样又常常在西方,因此从沿海看内地,从城市看农村,从上层看下层,以及从当下的中国看历史的中国,对于20世纪以来的知识人来说,便会在视野中和取向中比从中国看外国更远。就中国的知识人之所以为中国知识人而言,这种里外倒置同样是缺乏文化上的自我意识。
时至今日,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之中,从而正处在不断地由已知探索未知的过程之中。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又面对着一个充满猜疑的世界,并不得不回答种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问题。前者需要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后者也需要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因此,文化自觉不能不成为今日中国的一个要目。
(作者为华东师大教授)
《南方周末》 日期:2013年3月1日 版次:E30 作者:杨国强
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88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