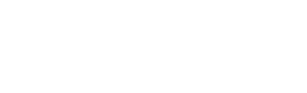近段时间,实践哲学构成了我思考的一个方面。与此有关的阅读,涉及面比较广。
实践并非一个新概念,从中西哲学的历史来看,有关实践的讨论绵绵不断。就西方哲学而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实践的理解主要与伦理政治领域相关。如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把知识或思想分为三种: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制作或生产性的知识,后者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生产技术性活动,但这种活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未纳入实践之域。康德大体上承继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他的实践理性首先和道德实践相联系。到了马克思,实践概念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马克思把劳动引入到实践里,将其作为实践的主要形式。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已经开始扩大了实践范围,但相对而言,这种扩展还带有思辩哲学的形式,与马克思基于现实的视野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对实践的理解是在广义上的“行”这一概念下展开的,中国哲学的早期经典,都从不同方面涉及“行”。《易》在宽泛意义上关乎对行动的预测,《礼》侧重于对社会生活中不同行为的规定、引导,《尚书》作为广义的政治文典,记录历史上多方面的政治活动,这些都与广义之“行”以及如何“行”紧密相关。在尔后的知行之辨中,“行”构成了中国哲学论辩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哲学中,“行”一方面涉及广义上的“赞天地之化育”、“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又更多地侧重于成己和成物,尤其是成己(成就人自身)的过程。
可以看到,中西哲学对实践或“行”的理解有相通之处。当然,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特点。到宋明之后,知行之辨逐渐与工夫和本体之辨联系在一起。在宽泛的层面,工夫既包括致知,也涉及人的践行,而本体更多地涉及人的内在精神形态和结构。中国哲学的主流肯定本体和工夫不可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涉及知和行的互动,这与西方哲学侧重于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的分野,在进路上似乎有所不同。但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比较早地关注广义之“行”或实践这一问题。
在现代哲学中,对实践或广义上的“行”也有不同层面的讨论。在分析哲学系统中,以行动理论或行动哲学为形态,对行动的理解首先与语言的逻辑分析紧密相关。就道德行为或道德实践而言,分析哲学中的元伦理学往往将道德现象的理解还原为对道德语言的把握。现象学,特别是其后来的发展,也对行动过程给予了不同形式的关注,如海德格尔便将人的生存过程提到很突出的地位,从现象学一脉出来的伽达默尔也重提实践哲学。另一个对行动与实践比较关注的哲学流派是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主义的重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对行动和实践的思考往往与反思马克思的实践理论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对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提出很多批评,认为劳动主要涉及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以成功等为目的,他所注重的则是主体间的交往行动,后者以所谓主体间的沟通、理解、共识等为指向。不难看到,以上理解都包含自身的一些偏向。
从学术或理论的层面来看,对实践问题再思考可以有两种进路。一是从不同的学科层面展开研究,如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等等。这些年来,政治、伦理等领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政治哲学、伦理哲学似乎已逐渐成为显学,哲学领域中在某种意义上浸浸然形成了实践哲学复兴的趋向。与之有不同侧重的是带有原哲学意义上的考察,如关于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实践推理等问题的研究。
以行动与实践的关系而言,行动的研究更侧重于对微观层面活动的分析,实践的考察相对来说更多地表现为对宏观的历史层面现象的把握。从“行”和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看,问题则涉及行动或者实践的具体意义。理解“行”或实践,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不能将其抽象化。在历史上,笛卡尔曾有“我思故我在”之说,一些学人为突出“行”对于“思”的优先性,提出了“我行故我在”。在我看来,这里的“我行”与“我思”一样,都带有某种抽象、空乏的特点,缺乏实质的价值内容。对“行”,我们需要从现实的层面,将其理解为成己和成物(成就人自身和成就世界)的过程。可以说,正是成己和成物的历史过程,赋予“行”以具体的价值内涵,使之不同于“我思”这一类抽象的概念。仅仅停留在“我行”这一层面,往往无法扬弃对实践的抽象理解。
从成就人自身和成就世界这个角度去理解实践,在逻辑上面临成己与成物如何可能的问题。按我的理解,成就人自身和成就世界的前提,首先是世界以及人自身的可改变性,正因为世界或人本身非“前定”或“命定”,而是具有可改变性,对于世界和人自身的成就才是可能的。这是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的。成就世界和成就人自身之所以可能,还和人自身的需要以及基于需要的目的和理想相联系。如果在人和世界或人和自身的关联中没有需要以及基于需要的目的和理想的引入,人就会面临一种对世界的冷漠。正是需要以及基于需要的目的理想,引导人走向对世界以及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关切,这种关切同时构成了“行”或实践的内在推动力。
对于世界的变革还涉及现实的条件,后者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就人自身来说,对世界的变革离不开人的内在能力。人具有理解和改变世界的潜能,这种潜能在人与世界的互动中,逐渐转化为一种现实能力,后者又构成人进一步改变世界、改变人自身的内在条件。在更广的社会层面,改变世界的现实的条件还包括社会体制、现实的社会关联(荀子所说的“群”)以及文明演化过程中的形成的各种工具、器物,等等。正是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使以成己与成物为内容的“行”或实践能够有效的展开。
在成就世界和成就人自身的以上过程中,“做什么”既与“是什么”相联系(变革对象之“行”以对象实际的“是什么”为根据),又与“成为什么”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与人“成为什么”基于人之“行”)。由此,“做什么”、“是什么”和“成为什么”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中华读书报》 日期:02月06日 版次:10版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链接: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2/06/nw.D110000zhdsb_20130206_2-10.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