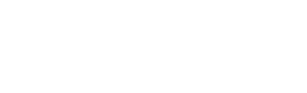《毛诗序》是中国诗歌理论批评最重要的文献,是儒家文艺思想的奠基作品,以及后世儒家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這样说当然不错,但是更应该加上一个词:“政治”。五四以来,对《毛诗序》的解读,基本上是否定的。关键是解释系统已经从传统的经学中心,转变成了现代的文学中心。然而只有从经学立场出发看,才能看到政治的文学及其正当性。孔颖达疏是对這一政治文学文献最详细周全的阐释,是最具有浓度和涵盖面的经典文本。读序不读疏,不容易真正进入儒家政治文艺思想的内部世界。解释学与人类学认为,要理解一种文化的观念,必须采取该文化持有者的立场,如何取得文化持有者的立场,解释者与对话者须采取他们的语言。细读孔疏,正是熟悉儒家文论的语汇,进入他们的语境之中,为更好地理解、阐释、纠正现代人的一些误读。這里先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批评史的观点,然后再以《毛诗序》毛传郑笺、孔疏的两段原典来展开讨论。
一、几种批评史的解读
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论《毛诗序》的历史地位:
“美刺”、“主文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等,這些理论……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利用诗歌艺术为政治服务、巩固秩序的要求。儒家有关六艺说的理论,虽注意到改良政治的要求。這里,《毛诗序》基本上定位为统治阶级的舆论工具,“发乎情,止乎礼义”,也成为了束缚青年男女爱情的礼教罗网。作者也肯定了《毛诗序》所包含的有关诗歌社会作用的理论,是先秦孔子、荀子和《乐记》的诗乐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但只是“从艺术的内部规律方面来总结,促进了诗歌的创作与批评的发展”,至于“政治”方面,是没有正面地位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更以“诗的汩没”为小标题,批评《毛诗序》的“美刺”:
《关雎》,《毛诗序》说是“后妃之德也”,虽异于齐、鲁、韩的说是刺康后,然究竟逃不出“美…刺”的故套,仍然不给予它以诗的位置,仍然给予它以圣道王功的奇迹。自然啦,《诗经》中是有刺诗的,但每一首都替它加上美刺的作用,而加上的美刺又以圣道王功为准绳,则《诗经》中的诗,得到了“不虞之誉”,同时也背上了“不白之冤”。
這也是五四时代普遍流行的以文学鉴赏取代经学批评的认知图式。比较新的一本诗论史是霍松林主编的《中国诗论史》,其中关于《毛诗序》的论述,是近年来最详细、最切近于汉儒思想情景的分析,也对于《毛诗序》集儒家诗论之大成,也有相当深入的揭示。然而却对《毛诗序》中“诗言志”的“志”,作了最严厉的批评:
所谓“志”,是封建的政治伦常之理为主导的情与理的统一。……情既然是欲,就不允许自由发展,否则就会流而及于乱,因此需要“制”,需要“节”。用以节制情欲的,只能是先王所制的“礼义”。礼义存于心,情有所动,立即就会受到节制而归于正,形之于言而成为诗,就一定会合于先王之道了。……《序》作者按照這样的基本原则去说《诗》中所有的诗,于是诗中所有的哀、乐、闵、伤、恶、怨、忧、惧之情,都归于正,都变成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非常有用的东西。這当然会给《诗》带来严重的歪曲和安排,但序作者根本就不可能顾及于此。
五四时的胡适他们,还承认“诗言志”是正当合理的,“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还用這种观点来批判《毛诗序》,然而在霍松林這里,“诗言志”变得更加“历史脉络化”了,也就是说,对于理论的遗产,不可能“抽象地继承”,只能进一步还原到历史的脉络中,使理论的价值只成为当时、当地、当下的价值,使其普遍成为殊相,通性成为个别,因而进一步使价值虚无化。這就甚至比五四时胡适他们对诗序的否定还要厉害。所以,20世纪对《毛诗序》的否定,基本上是两个悖论的方向,一个是“历史脉络化”,即将其尽可能求真求实,祛魅打假,将价值还原为汉儒的时代具体要求,另一个是“去历史脉络化”,即脱离当时最大的话语背景,即汉儒的经学解读立场与五四人的文学解读立场或史家求真立场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他们最大的策略,即打破《诗经》的经学身份。胡适在1925年的《谈谈诗经》中说:
从前的人把這部《诗经》看得很重要,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這个观念,假如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郑振铎视《毛诗序》为首要摧毁目标的说法,也代表了五四新文化的使命:
《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的附会诗意,穿凿不通。……压盖在诗经上面的注疏的瓦砾里,《毛诗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读毛诗序》,《古史辩》(三)
然而,当时就已经有人看出了他们并非全然正确,而是有时代局限的,如章太炎批评说:
“古史辩派”的五蔽:一日尚文辞而忽事实,………五日重文学而轻政事。(《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
罗根泽也比较清醒指出了五四文学观念的时代性,虽然他自己也逃脱不了這种成见:
成见的养成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是时代意识。譬如五四以前的文学观念是载道的,由是《关雎》便是“后妃之德也”(毛诗序)。五四以后的文学观念是缘情的,由是《汉广》便是孔子调戏处女的证据(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卷一第一章第二节)。……五四的学者,因为时移事改,知道了古人之以传统的载道观念曲解历史,却不知自己也正作曲解历史的工作,不过不依据传统的载道观念,而改依五四的缘情观念而已。(《周秦两汉文学批语史绪言》)
应该说,五四新文化的诗经学,继承宋人与清人诗经学中的文学派,从文学的角度上重新解释,将《诗》还原到诗的源头,大大开发了中国抒情文学的传统资源,有利于新文学的创造,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但是,必须承认,《诗经》除了文学的意义,还有经学的意义;经学的意义,也自有其两千年的历史价值,不因文学的意义而受到遮蔽甚至抹煞。因而,如果要理解中国诗经文化的主流传统,重新恢复从经学批评的角度去同情地理解《毛诗序》這篇文献,是十分必要的。
二、原典解读
(一)《关雎》
《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孔疏:《诗》理深广,此为篇端,故以《诗》之大纲并举于此。
第一个问题是:《关雎》是“恋歌”,还是“后妃之德”?
《关雎》是20世纪最普及的诗经作品之一,但最流行的解释是所谓“古代恋歌”。然而从汉代到清代,几乎没有人将這首诗解释为“恋歌”。为什么呢?关键是,《诗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它的经学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文学意义。如果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来看《诗经》,就不会有男女“恋歌”之说。《关雎》经学传统的解释,主要是“美德”,或是美文王之德、或是美后妃太姒之德。而五四时代,几乎全然颠覆了传统解释。胡适说“《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他用了各种勾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乐以钟鼓,這完全是出自那时的民族风俗”。郑振铎《文学大纲》认为此诗是“民间歌谣”,是“流传于孺妇农工之口”,无名氏的集体创作。从传统解释到现代解读,从作者、写作时间到诗旨,现代人从文学的角度重新开发《诗经》,其中最不易察觉的一个颠覆是改变了《诗经》的读者对象。即将原本对统治者发言的经学,改变成了对普通文学读者发言。如果《关雎》是对统治者发言,那么“美德”说就很好理解了;如果是对普通文学读者发言,当然是“求爱”说更好理解。然而在今天看来,“文学”对“经学”的颠覆,不过是五四时代现代文化的新叙事,是一种“文学优势”、“民间想象”的话语建构,用以达成新文化摧毁旧文化的根本目标。表面上看起来是“文学”,其实是“政治”。因而五四新文化诸君的科学整理国故,还历史真面目,其实“科学”与“历史”都谈不上。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即针对五四过于文学化、民间化的新说,以语言学、历史学、比较诗学等多元进路,破民间重心说,破国风男女之辞为本来面目说,颠覆“五四”,直捣朱子,回返了汉儒与先秦儒家诗学之义谛。自此,《诗经》非民间歌谣,渐成为学界常识。林庆彰认为,历代有两次废《诗序》的运动,一是宋代以朱熹为首,一是民国以胡适、俞平伯、郭沫若为主的,但是两次都失败了,《毛诗序》屹立不摇。他们失败的原因是,《诗序》很大部分是有根据的、可靠的,既使是国风,朱子定的诗旨也有百分之七十合于《诗序》,何况是雅颂,仅仅靠解释几首风诗的民间性质,不能整体上废去《诗序》。其次,《诗序》不止是一种史的事实,而且是一种儒家理论与思想的建构,在儒家思想占主流的时代,《诗序》不可能被废。林氏的這个大判断是相当中肯的。我要补充的是,在五四时代,批判儒家思想的《诗序》,是五四时代文化政治的需要;但是随着儒家传统思想的重新回返当代中国思想与生活中,《诗序》也不可能被废。
孔疏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关雎》言后妃之德,怎样“深广”?何以“大纲”?
1、人伦大端即文明开端
孔疏: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风,实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是以《诗》者歌其性情。阴阳为重,所以《诗》之为体,多序男女之事。
孔疏:风为夫妇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
后妃之德,即文王之化的具体体现;文王之化,即文明开端的具体体现。故,“风”即文明发端。即一个国家的政治与道德的基础,所以称为“生民之本,王政所重”。从“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這两句来看,很明显,是讲给统治者听的,至少是统治者的后备人才听的。与《论语》中齐景公问政,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样的意思。“经”是“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礼记》)的文字,不是男女私情,所以从文明开端说起,很合理。
2、士人主持文明开端
郑笺:“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正义:风之始,此风谓十五国风,风是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风天下”,《论语》云“君子之德风”,并是此义。
孔疏:周公制礼作乐,用之乡人焉,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国焉,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
這个“始”有两个含义,一是夫妇为天下之始,易曰:有天地而后有男女,有男女而后有夫妇。一是文明发端。孔疏:“风之始,谓教天下之始也。”风是士人主体。谁是风的发动者?孔疏说是周公。周公即“君子”的代表,即士人主持政权的代表。表明风的来源不是统治者,也不是民间,而是知识人即君子。這里有知识人话语权的自觉。這一含义十分重要。
从“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来看,《诗》的功用,不是用来阅读,而是用于礼乐的场合。因而《诗》义发挥有两个向度,一是由乡大夫而民众,一是由诸候而群臣,這表明:君子即知识人主持的文明教化,一是向着社会的,一是向着统治者的。前者是知识人在世间的文化责任,后者是知识人的政治责任。抗议精神、批判力量,皆由此而来。
五四新文化诸人,将《诗经》的对象变成了文学读者,作者变成了民间歌手,内容变成了求爱与勾引,完全失去了《诗序》向着政治生活发言的严肃深义。
3、道德优势
孔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沈云:“上风是《国风》,即《诗》之六义也。下风即是风伯鼓动之风。君子风教,能鼓动万物,如风之偃草也。”今从沈说。
《论语》: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义曰:此章言正乐之和也。《关雎》者,《诗?国风?周南》首篇名,兴后妃之德也。《诗序》云:“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是乐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哀而不伤也。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正乐之和也。
《论语》、《诗序》义脉相交,相互发明,“哀乐”皆政治生活情感;风教、风义、风化,皆道德优势。表明诗歌道德情感的自觉(最早的诗歌没有道德意识,只有原始人欲。《关雎》中夫妇以专贞忠诚的雎鸠为榜样,已经有了道德意识,《毛诗序》更提炼出种种政治生活中的道德感:和谐、尚贤、勤勉职事等,孔疏更将其提炼为道德情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明不是民间、原始的、朴素的,未经理性提炼的感性文化资源(胡适说的所谓“他用了种种勾引女子手段……,意大利、西班牙几个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窗下弹琴唱歌,取欢于女子;至今中国的苗民还保存這种风俗”),也不是官方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士人的道义优势。
我们从前解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着眼于儒家诗学“中庸的情感原则”,不是不对,只是还不够还原到原典尤其是《毛诗序》原典的意思。读孔疏才知道,原来“乐而不淫”的真正意思是,不自我陶醉沉湎于外在的好听、好看、好玩之事物之中,尤其是不要被巧言令色的佞臣所蒙蔽,而是要知道乐不忘忧,不忘寻找与使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哀而不伤”也不是不过度悲伤的意思,而是苦思冥索地企求贤才,永无伤善之心。這对于一个深悉权力滋味的领导者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关雎的言说对象分明是统治者,這是政治道德的大事。《毛诗序》其实是政治哲学。
下面讨论中国文学批评中政治伦理批评优势的正当性。其一,政治和伦理的批评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背景中,并不是存在于文学家写作活动之外的批评,而是内在于其生命本身的批评活动。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家最基本最主要的生命活动与精神寄托,就是政治活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普遍的人生道路,政治上的失意与得意是他们最真实的情感内容。文学批评一方面要知人论世,切近地抉发出文学家最真实的创作动机与兴奋点,另一方面也要引发共鸣,切实地进入当时读者的文化脉络之中,而政治伦理正是這个兴奋点与文化脉络,這即是政治伦理批评得以存在并传承的合理性之一,這也是《诗序》得以千年传承不废的理由所在。其二,文学创作贵在言之有物,言之能深,而文学批评发现表面语言背后的深度含义,推崇文学写作能有真感、实感,能对时代病痛作批判性的书写,恰恰是文学本分内的事情。其三,如果我们不以后世分化的文学观看,如果我们将儒家文评如其自身而然地视为一种政治哲学或政治艺论,更进而言之,如果我们不把政治视为一种不干净的、野心家或政客的事情,而视为公民的事情,尤其是公民中的精英们的重要事情,那么,中国文学批评中政治优势的正当性,可以与西方亚里士多德、葛兰西、阿伦特诸家的政治学思想相对话,而取得一种现代政治思想的正当性。我们不妨再回到《毛诗序》的文本。
(二)美刺
1、一国与一人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正义曰:“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辞,言诗人作诗,其用心如此。一国之政事善恶,皆系属于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诗者,谓之风。言道天下之政事,发见四方之风俗,如是而作诗者,谓之雅。言风、雅之别,其大意如此也。……故《志》张逸问:“尝闻一人作诗,何谓?”答日:“作诗者,一人而已。其取义者,一国之事。变雅则讥王政得失,闵风俗之衰,所忧者广,发于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
2、正人君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孔疏:普正人之得失,非独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诚能用诗人之美道,听嘉乐之正音,使赏善伐恶之道举无不当,则可使天地效灵,鬼神降福也。
“普正人之得失”,但重点乃在于重君,因为君的影响大。正人君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孔疏又说:“说刺诗者,以诗之作皆为正邪防失,虽论功诵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说作诗之意耳。诗皆人臣作之以谏君,然后人君用之以化下。其教从君来,上下俱用,故先尊后卑。”诗歌文学的政治性,首先体现为对最高统治者的批评,矛头是对上的。后来人指责儒家文艺思想为统治者服务,是没有客观了解的乱说。
3、发乎情止乎礼义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孔疏:哀伤之志,郁积于内,乃吟咏己之情性,以风刺其上;陈王政治,或指世淫荒,虽复属意不同,俱怀匡救之意。
我十一年前写的文章里说过:“首先,在《毛诗序》的语义系统中,‘礼义’与‘政教’不等同。孔疏:‘礼义言废者,典法仍存,但废而不行耳。’‘礼义者,政教之本,故先礼义后政教’。用今天的话来说,礼义是道义精神,宇宙原则,而政教是现实话语,权力原则,思想规范。其次,发情止礼,是说变风,特指偏主于政治批判的诗歌;匡正人君成为這类诗歌的根本宗旨。换言之,用這句话指表达男女之情的诗歌并不符合《毛诗序》原义。第三,批判政治,匡正人君,是不是要遵守某种统治阶级的思想规范?恰恰相反,礼义不是来自统治者的规范,而用来‘规范’统治者行为的道义原则,是让统治者合乎礼义。发乎情止乎礼义,完整地说是:变风的情感,发自人民的性情;匡正人君的目的,是回归天下有道的礼义。孔疏以‘哀伤之志,郁积于内,乃吟咏已之情性,以风刺其上’解释‘发乎情’;用‘或陈王政治,或指世淫荒,虽复属意不同,俱怀匡救之意’来释‘止乎礼义’,最得毛公原义。礼义,即普遍、共通的人性常道。可见,這本来是一个极富思想光采的经典命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变成了儒家思想钳制人民自由表达的反人性教条,走向了這一命题的反面,起毛公孔颖达于九泉之下,岂不冤枉哉!”(《出新何术得陈推》,《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二期)
接下来我再对上述内容的理论意义,略加引申阐说。
三、今解:公共性、话语权与变今之俗
第一,充分的公共性的文学。“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一国之事,表明不是小我一己之私,不是原子式封闭的个人世界。一人之本,表明创作生命的来源,发自诗人的真情实感,扎根于真实的一己生命体验。充分的公共性,而不只是私人性个人性。因而,我们今天重读《毛诗序》,反省中国古代文学政治批评优势的传统,再认识《毛诗序》所代表的关注政治生态与世道人心的公共性,有助于重建具有公共关心度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就比空洞、形而上学的存在主义与以沸止沸的非理性思潮更为具有真实的时代对话意义了。
第二,“风、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则一国皆美之,一人刺,则天下皆刺之。”這里高度肯定了诗人的话语权。自古以来文学就有话语权。文学的话语权体现在广义的文学可以赋予政治权威以更高的价值,有思想有关怀的文学家可以参与赋予政治权威以正当性。如果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文学传统影响的文学政治观,将文学简单、绝对地理解为政党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文学的政治性理解为政党的传声筒,深深伤害了文学的自主生命,那么,新文学的另外一支传统,即深受西方文学自主思想影响的现代文学观,基本上放弃了文学家可以赋予政治权威以更高的价值這一理念,从而坠入纯文学的神话陷阱之中。纯文学的观念,其实也是一个现代神话,经不起真实生活现实的考验,一旦遭遇压迫,难免会戳破神话。新文学的干将胡适晚年深受国民党专制之苦,曾对殷海光说:“我认为我们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因为我们有权有势,所以才会受到种种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压迫”,“穷书生拿了笔杆在白纸上写黑字而印出来的话,可以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好感,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這个就是力量。所以我们這一班请愿主持言论的人,不要太自卑,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這个立言有权的思想,正是来自古代中国传统中人文可以经天纬地、弥纶彝宪,文学可以“鼓天下之动”的思想。這正是《毛诗序》传统的文学政治大义。而這一传统,已为全盘吸收西方文学理论优势的20世纪80年代文论思潮所抛弃。
第三,美刺批评的传统诗观,来源于孔门诗教的善善恶恶,是儒家的是非大义。《毛诗序》以及它的思想源头孔门诗教,其言说对象是那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巨变时代,旨在建立文明与文化基本价值的时代,尤其是变风变雅,王道衰、礼义废、国异政、家殊俗,天下无道,是那个时代的真相,而“变今之俗”(孟子)是儒家的重大使命。所以他们不得不大声疾呼,不得不黑白分明,不得不善善恶恶,不得不以“美刺”批评为主调。而我们這个时代,不能不承认是一个巨变的转型时代,是一个价值迷失甚至是价值虚无的时代,原有的东西已经遭损、破败甚至毁灭,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我们這个时代由于处于转型时代的空白期,精神质量的下坠异常真切,人性的堕落非常容易,社会公道与正义非常虚弱,世道人心极其脆弱,在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需要研究与考察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但是我们更特别需要广义的文学這样鼓天下之动的力量来重振人心、经纬天下,因而,重建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奠定一种新的政治与道德的基础,是我们這个时代与秦汉之交那个时代的相似性,因而,《毛诗序》所涉及的并不太复杂的人性主张与文明底线,以及它所主张的善善恶恶的批评观,就与我们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观有了某种重要的相关意义。
最后,正人君的抗议精神,其对象是统治者,体现了中国文学思想传统最有风骨的一面。而這一种传统,在近现代无可挽回地流失了。《毛诗序》所代表的真精神,魂兮归来,还有待于后人。其它如“先王之泽”,“文王之化”,皆可与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中“文化权威”相对读。可见,《毛诗序》涉及的问题其实十分丰富,诸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中的个人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文学与公民的关系,文学与文化权威的关系等,其核心价值是:抗议精神、道义原则,以及這里没有提到的温柔敦厚的人格理想、时间与人事的诗学旨趣。通过充分的古今对话,完全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思想的资源,发展出一套本土的政治文化批评的理论系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新华文摘》 2012年第5期(第90—93页)作者:胡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