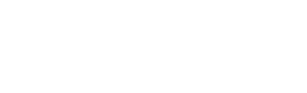“人猿相揖别。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毛主席《贺新郎·读史》)自此以后,人类文明迅速演化,而今日变化之剧更胜从前。我们不妨大胆发问:人类文明内部是否也可能发生新旧相揖别的事件,而现在就已经到了那一时刻?“君子而时中”(《中庸》),理论工作者也需要“时中”的品格,通过运思来切中“时”,切中时势及时代精神。尤其重要的是,思考中国道路,需要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演化脉络中理解我们现在身处何“时”,思考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以及中国在此趋向中的位置与天命。
或许,我们正身处人类文明的后经学时代和新奇点时代。
冯友兰曾将中国古代哲学史分为“子学”与“经学”两个阶段,相信随着西学东渐,经学之旧瓶逐渐难以装下西学之新酒,经学之旧瓶终破而经学时期亦终。冯友兰所讲的“经学之旧瓶”乃中国传统经学的旧瓶,但我们所讲的“后经学”之“经学”还包括奉西学为圭皋的经学:将西方理论不加批判地奉为绝对真理,用作推理过程的大前提。中西两种异质思想传统的相遇,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古今中西”之争,任何单一传统中的经典都不再具有绝对的、惟一的真理性。真理的历史性与文化相对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开创中国道路的前提之一,便是克服各种形式的经学独断论。
冯契先生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问题乃是:在“古今中西”之争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 以文明论的视域观之,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问题也许可以表述为:在“时空压缩”背景下,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而中国在此趋向中居于何种位置,应当承担何种天命?“古今中西”经“时空压缩”(传统、现代、后现代意义上的“时”之三维;包括中、西、印等等在内的多元“文明空间”) 之后进入“时空坍陷”,进而产生新的“奇点”,人类文明迎来全新的开端。人类文明的新奇点时代,有别于雅斯贝斯所讲的不同文明彼此隔绝、独立发展的轴心时代,也有别于亨廷顿所强调的文明冲突。
中国迎来了人类文明的后经学时代和新奇点时代———这是说,人类文明的后经学、新奇点状态可能首先在中国发生。中国道路的意义与使命即在于此。中国道路同时肩负着两种看似吊诡的任务: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然而,也许事情的奇妙之处在于,中华民族只有超越民族视域才能实现其“伟大”之复兴。中国不能只是现在通行所理解的民族国家,而应该是一种后民族国家、一种走向人类组织的新形态的过渡者。再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维度,不仅要超越民族国家,还要超越特定文明形态。所谓“超越”,不是外在的“超越”,而是据而有之的“扬弃”:一边是现有的中、西、印等诸种文明,一边是正在形成中的新人类文明,二者处于动态的辩证结构之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将现有文明形态涵摄为内在的“道术”。“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大道,每下愈况,遍在于、且只能分裂于诸种有同有异的方术之中;然而,“道术为天下裂”,不是道的蜕变,而是道的现实展开。
如果从“后经学”“新奇点”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及其时代精神,中国的学人当采取何种与之相应的思想姿态? 也许,中国的学人可以把自己理解为人类新文明的开拓者与承担者中的一分子,把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同时视为希腊、希伯来、伊斯兰、印度等等诸种文明理所当然的继承者,从人类文明正在展开的气势磅礴的实践中汲取洪荒之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运思,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继往开来而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