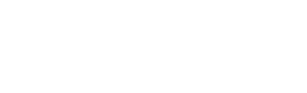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留有名言:如若要了解一个时代,则要洞悉身处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是反映时代风气最为重要的象征。
被誉为本世纪初以来最具影响力和社会情怀的历史学家,美国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的创始者,著名思想家托尼·朱特(1948-2010)称得上是与时代并肩而行,并能彰显时代特性的知识分子。
近期,托尼·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事实改变之后》出版,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才能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阅读朱特的列车始发站
洞察之于时代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通过优秀历史著作及其研究,走进纷繁复杂的往昔世界,从历史中找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待解之问;更会感知历史学家自身的时代体悟,感悟时代赋予他们写作背后的道德伦理与思想悸动,感受他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激情与困惑、局限或遗憾。
让我们看看历史学者托尼·朱特的思想轨迹,他生前撰写的《战后欧洲史》(2005年),被公认为是这一领域最具宏大视野和开拓性意义的现代史学经典,厘清并极大提升了世人对于现代欧洲历史和当下紧迫问题的洞察能力。我们可以从朱特的书中,找寻到目前欧洲社会所面临困境的全部历史根源。
除此之外,朱特也是一位勤奋和高产的媒体专栏作家,他为欧美主流报刊和思想刊物,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纽约书评》撰写了大量思想文化随笔、深度书评和国际时事评论,其文风兼具知性和强烈的批评意识,笔端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愫与道德责任感,被描述为“叙事强如海涛,论战笔锋更盛”,总能够通过发现“未知的真实来修正历史,从而洞见未来”。尽管西方思想学界和部分政治精英对于朱特的思想遗产存在争议,甚至不以为然,但对朱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时代感和勇于表达的真诚特质则众口一词,由衷地感到钦佩。
对于那些并不知晓朱特人生经历,未曾阅读过《战后欧洲史》的读者而言,选择从他的一系列时事评论、书评文章和访谈实录入手,或能更容易进入到他的思想世界。自2001年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的肌萎缩侧索硬化(俗称“渐冻症”),朱特在家人友朋的帮助下,以惊人的坚持和毅力,克服身体上的巨大痛楚,奋力著述。在付梓《战后欧洲史》这一磅礴巨著之外,朱特先后出版了被人称许为临终三部曲的自传式思想文集,分别是《重估价值》《沉疴遍地》与《记忆小屋》。朱特去世后,由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记录并与朱特访谈对话的著作《思虑20世纪》也告出版。值得庆幸的是,以上作品皆有优秀中译版本发行,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全面、客观地了解朱特不平凡的思想与人生历程。
但以上著作与选集并未涵盖朱特的所有思想印迹。2015年,由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所编辑的文集《事实改变以后》出版,收录了从1995年朱特成立雷马克研究所到2010年朱特病逝这段时间内发表在欧美主流思想刊物,特别是《纽约书评》上的一系列未曾结集出版的随笔和书评、时事评论,以及部分未刊登的作品草稿。按照霍曼斯女士的说法,这本文集可以让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朱特写作的初心:在那些锋芒毕露、论辩酣畅、批评深刻的思辨文章背后,究竟是怎样一个怀有“真诚之心”的写作者?《事实改变以后》这部文集,对于熟悉朱特思想谱系的读者而言,阅读可以再次加深他独有的叙事风格带来的思想亲切感;对于初次接触朱特作品的读者而言,本书可视作一部得以窥见朱特精神全貌的观念小手册,是日后阅读朱特系列作品的列车始发站。
不平庸也不愿随波逐流
无论参与何种领域、何种话题,托尼·朱特始终坚持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强调史实、尊重事实,成为他涉及公共性话题时所坚守的写作准则。喧嚣与动荡并存的二十世纪,加之朱特多元而独特的人生经历,共同塑造了他作为历史学者的技艺与修养。
朱特出身于战后英国伦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青年时期热忱于犹太复国主义,曾和其他犹太青年共赴以色列开垦定居点,犹太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激进色彩在朱特身上有着鲜明展现。得益于战后经济复苏与福利制度的有效运行,少年时代的朱特得以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熏陶,养成了终身受益的文学修养和写作习惯,博学而进取多思,善辩而不乏克制,批判之余亦善于自我嘲讽。朱特曾自我剖析,这种典型的英国思维风格,是他能够抵御各种极端主义思想倾向,持续并公允讨论各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议题的能力所在。保持冷静、独立前行对于托尼·朱特而言绝非一句口号,而是一以贯之地加以实践。
在《事实改变以后》的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感受到朱特对于当代历史研究和历史学家的深度剖析与犀利批判。譬如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作品《极端的年代》的解读,就极具代表性。说来颇有意思,朱特当年作为本科生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历史学时,作为前辈师友的霍布斯鲍姆一度是他崇拜的学术偶像。但随着20世纪下半叶欧洲历史进程的演变和冷战的终结,朱特发现这种新的时代特征的转变与扩散,并没有在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中得以彰显。那种老派的左右之分、进步与反动对立、发展与落后的二元思维模式依旧顽固存在,面对新近发现的历史事实,霍布斯鲍姆仍然选择涛声依旧。对此,朱特在摇头扼腕与公开批评之余,颇为怀旧式地引用1968年他在聆听霍布斯鲍姆讲座时所记录的那段话,“有时候,关键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去解释世界。但为了解释世界,我们要对它的改变方式抱有同情”。朱特用这种夫子自道式的宽慰,既向前辈表达足够的敬意和理解,亦在不经意间为日后自己的历史研究确立了方向。
冷战结束后,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职业史学领域持续陷入碎片化和后现代思潮的论述之中,在历史学家圈中,看不到对于历史真实的讨论,取而代之的是对各种历史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讨论,历史研究愈来愈陷入各种细枝末节,痴迷于各种所谓转向,却把各种大历史的书写机会拱手让给其他学科。另一种倾向是用所谓的政治正确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来概括和描绘被冷战遮蔽的地区发展和历史进程,这种倾向在描绘战后欧洲,尤其是中欧、东欧的历史过程中尤为凸显。
有感于两种倾向的消极意义,朱特坚持历史研究应该重新迎来宏大主题,用真正的历史事实来重新书写那些容易被遗忘、被忽略的事物。朱特认为历史学家不能沉溺于圈中的同行学术评议,而是要尽可能把研究作品放置在公共视野当中加以评判,既不能孤芳自赏,也绝不回避论战。在本书中,霍曼斯女士选编了多篇具有代表性的书评作品。在为冷战史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我们现在知晓:一部新冷战史》所撰写的书评中,朱特赞许加迪斯勇于使用诸多新近发现的档案来修正冷战起源的诸多论说,其中就包含加迪斯本人的旧说,体现出历史学家尊重史实,勇于改正的品质。同时,朱特也提醒我们不能热衷于发掘档案,唯档案是从,从长时段的角度冷静回顾和观察冷战历史依然是需要和提倡的。而在另一篇书评综述中,朱特毫不客气地批评冷战结束以后,诸多西方历史学者对于东欧历史写作陷入一种自我想象的循环之中,要么把东欧描述成为美苏大国对峙之下的没有历史存在感的区域,要么过度夸大东欧在推动苏联解体上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因素,并赋予其理论化。朱特认为,无论是运用疏离异乡的笔调,还是运用他者浪漫化的描述,都无法给予公众一个真实全面的东欧,历史学家不能仅凭情感和善意用事。而在另一篇火药味十足的书评中,朱特集中火力抨击牛津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的巨著《欧洲史》,批评他虽然以东欧历史为研究专长,却根本无法向公众呈现出一个严肃的欧洲发展历程和东欧地区多维复杂的历史原貌,加之存在不少事实谬误,实在是失败之作。这篇书评发表后,自然招致戴维斯的反唇相讥,两人之间的笔战时有碰撞。但这并不妨碍两位历史学家间的惺惺相惜。日后,戴维斯对朱特的《战后欧洲史》赞不绝口,认为其著作乃是无法超越的当代经典,远胜于其他同类著作,病榻上的朱特则回信表示感谢。两位历史学家间的君子之谊令人敬佩。
诊断每况愈下的时代症候
如果说朱特在“扮演”历史学家时,体现的是不甘平庸,勇于抗拒大众潮流的品质,那么他以评论家的身份,投书欧美主流媒体,通过时事评论和各类政论文章,对西方世界存在的诸多时代症候加以诊断,则体现出一种非凡的公共责任感和忧虑意识。颇为反讽的是,让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来诊断面临诸多沉疴的西方世界,这个事实本身就颇具悲剧色彩,令人唏嘘。
朱特在上世纪80年代来到纽约大学执教,在90年代中期加入美国国籍。一个并不需要讳言的事实是,朱特曾经对克林顿时期美国干涉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冲突表示欢迎,并对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论述表达了自己的赞许观点。然而,随着新世纪“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美国外交单边主义的全面兴起,以及接踵而至的伊拉克战争等事件,让朱特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身份窘境,不少朱特的思想“对手”嘲讽他悄然成为了真正的美国公民,他也不再称美国为“他们”,而是“我们”,这位曾经的欧洲知识分子,俨然已经开始讨论起“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免令人错愕。
面对这一系列诘难,朱特并没有用立场加以回应,而是坦然接受事实的改变。这也是朱特当年选择纽约,选择建立雷马克研究所的初衷。朱特始终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欧洲内部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并非如外部所了解那般线性与进步,而是充满了血腥与动荡。包括学者在内的西方公众,都有重新发现、认识、进而重新理解欧洲的紧迫历史责任感。除此之外,加深世界对于欧洲变迁的深刻理解,也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任务。这段时间正是朱特撰写他的传世之作《战后欧洲史》的时候,即使在这样的时刻,朱特依然坚持在公共舆论发言,帮助公众审视并观察变动中的欧洲与世界。
实际上,朱特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于他的欧洲情结与美国身份,而是他作为犹太人对中东问题的冷峻点评,这点体现在他对以色列处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审视犹太人的悲情历史与民族神话,批判美国犹太利益集团时那种一针见血式的诊断。他忧虑并警告以色列放弃对于“大屠杀”的念念不忘,谏言平庸之恶终有一天会成为世人对以色列执政者和民众的指摘。对于朱特而言,作为受难者的以色列身份不是可资利用、用之不竭的记忆神邸。以色列必须从长远角度思考与阿拉伯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而不是被国内的利益集团所绑架。
“让火车回归”
在朱特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念念不忘他儿时所乘坐过的英国火车,以及他在欧洲大陆旅行时,搭乘过的各国火车。霍曼斯女士回忆她赠送给朱特的最好礼物,当属一份托马斯·库克欧洲时刻表。带着这份列车时刻表,朱特夫妇畅游了整个欧洲,并对欧洲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在本书中,霍曼斯辑录了两篇朱特怀念儿时乘坐火车的回忆性文章,呼吁当下的欧洲和美国需要重新建设现代化的火车体系,因为没有火车的社会,自然就不会拥有良好的公共生活,所谓的共同体精神也就无路可循。
事实上,所谓的让火车回归只是朱特的一种美好愿望,一个以公共福祉与民众保障制度建设为主旨的国家意识的缺失,才是朱特心之念之的重大问题。朱特生活在战后欧洲经济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也正是欧洲福利制度运转最为顺畅的时代。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国家愈来愈被视作一个侵犯个人权益的对立面而不断遭遇削弱,成为各类政治话语与修辞中竭力躲闪的名词。
对此,朱特表示出最为强烈的倡议诉求,在他生命即将终结的那段时间里,他不断告诫他的读者和纽约大学的年轻学生们,通过百余年建设而成的服务型国家并非个人和创新的最大敌人,一个能够提供公共福祉、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福利的国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责任的体现。任何个人组成的集体,若没有共同的目标和机构,都将无法长存下去。重新思考国家的作用,需要来自从政者和公众具备相同的价值共识。
朱特临终的倡议值得我们深思。环顾当今的世界,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怀揣民粹情绪的民族主义蠢蠢欲动,一个兼具从政者和公众高度共识的国家从何而来,何以可能,何以建设,都是值得今天的我们,特别是熟悉朱特作品的读者所应深思的。